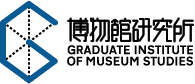活動報導
【法國連線】櫥櫃與園林:自然史展覽的兩個原型
-
關鍵字

作者/張婉真(法國新索邦大學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物館多樣性與其演變研究計畫客座研究員)
展覽史的研究近來日益受到重視,其中一個專項為有關自然史展覽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文獻主要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且多帶有博物館誌的性格。語言以義大利文為多,法文、德文其次,時間帶經常無法連貫,片斷破碎。因而我們需要綜合各家之言,方能串連一個可能的展覽史概括。出於一個希望能從古典時期開始梳理的企圖,筆者在目前非常初始的階段,先提出兩種展覽原型的觀察。
由於文藝復興之前的博物館或收藏歷史沒有留下圖像,雖從記載可知有供奉的行為,符合展示的意涵,但難以考察實際上展示的樣貌。若論文藝復興,Eileen Hooper-Greenhill(1992)認為歐洲第一座博物館為十五世紀的麥迪奇宮殿 (Medici Palace),這座宮殿也是這個時期的私人收藏中留有相對豐富的紀錄者。根據曾在1459年參觀過這座私人宅邸的米蘭公爵Galeazzo Sforza的記述:
書房、禮拜堂、接待廳、房間以及花園,所有空間的每一面都以黃金以及精美的大理石建造裝飾,房子的每一張椅凳及地板都飾有最傑出完美的大師所創作的繪畫及鑲嵌;有數不盡的掛氈以及金銀的家徽、銀器與書架;房間與接待廳的拱頂或天花板裝點著各種不同造型的金飾。(Alsop, 1982:366)
由此可見其華美精緻。麥迪奇宮的內部也有紀錄可考。根據一份著於1492年的清冊,可大致還原其內部的陳設概況,包括一樓的大廳、以及二樓的房間的家具。清冊也註明收藏內容,包括繪畫、雕刻與器物等。Hooper-Greenhill建議以傅柯的知識型概念理解從此一時期開始的私人收藏。她指出文藝復興的知識架構係以符應(correspondances)系統詮釋,其中占星術是其知識型很重要的部分。此時其知識的建構包括符號與相似性的交互指涉,且魔術內蘊於知識之中(Hooper-Greenhill, 1992:37)。
麥迪奇宮殿可說開啟前博物館的時代。類似的私人收藏到了十六世紀,在歐洲已經更為普及。Impey & MacGregor (1985:xvii)編著的重要著作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在一開始的導言中,節錄Francis Bacon寫於1594年在Gesta Grayorum的一段話,是非常有意義的:
首先,一座完美且收藏廣泛的圖書館,其中有所有智者的著書,可充實你的智慧。其次,一座寬敞、美妙的園林,其中不同氣候以及不同地區的各種植物,不論是野生或是人工栽培的,都受到保護:這座園林建有畜養所有稀有動物的房間以及所有稀有鳥類的籠子;尚有兩個相鄰的湖泊,一個是淡水一個是鹹水,以適應不同的魚種。如此你可以在小範圍內擁有一個私人的小宇宙。第三,一座良好且巨大的櫥櫃,其中有各種人為的稀有的藝術或器械,各種從自然中鍛鍊的,可以被保存、分類以及收納的形態。第四是一座廠房,配置有機器、儀器、爐具以及容器,是煉金術師的宮殿。
此段話語明確界定當時理想收藏的樣貌,特別是之中提出的園林(garden)以及櫥櫃(cabinet),更是日後博物館發展的原型。所謂的cabinet有不同層次的意涵。在文藝復興晚期,首先指一種用以收藏物件、帶有層架與抽屜的櫥櫃。在更晚期,cabinet一詞可用來同時指收藏物件的櫥櫃或是收藏的內容,以致延伸到收藏的空間以及整個收藏。如此cabinet與collection幾乎可以互用。更令人容易混淆的是,cabinet並非是十六到十七世紀用以描述收藏的詞語,諸如studio, studiolo, guardaroba, 或museo, galleria等也都常見。(Laurencich-Minelli, 1985:23)
(一)型態:櫥櫃
接續麥迪奇宮殿的發展,十六世紀後期弗朗切斯科一世·德·梅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的房間(Studiolo)是此時期最有記錄也最重要的收藏室。這間由貝納多·布歐塔列提(Bernardo Buontalenti)設計的收藏室,是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周圍是封閉式的櫥櫃,無法看到裡面的物品,之內用以收藏「稀有與珍貴,兼具無價與藝術性的物品,如珠寶、錢幣、加以雕刻的寶石、水晶、花瓶、精巧的作工、及不太大件的物品的房間。」(Lach, 1970 :40)由於藏品被封閉在櫥櫃之內,因此在每一櫥櫃的表面以繪畫或雕刻象徵收藏的內容,以方便進一步的搜尋。櫥櫃的分類以物種或材質為原則,承襲自老普利尼(Pline l’Ancien)以來的傳統(Pline l’Ancien, 1999)。
許多學者將這間studiolo與同時期卡米樓(Giulio Camillo)的「記憶劇場」相互比較(Yates, 1966:139),認為兩者的設計概念極為相似,應是前者有意參考了後者(Olmi, 1985:7; Hooper-Greenhill, 1992:105)。
根據Fraces A. Yates的研究,記憶劇場的設計以羅馬劇場的形制為原型,但不同的是,觀眾與舞臺的關係是倒過來的,也就是觀眾站在舞臺中間,知識位於觀眾席上。劇場被分為七個半區,每個半區都有七層,人類的所有知識被投射並保存在這個半圓形的分層結構中,是座記憶宮殿,意圖以一個理想的結構定位並管理人類現存的所有知識。記憶劇場的見證:
整個作品是木頭做的,之間放置著許多圖像以及小盒子;有不同的次序以及排列方式。[…]卡米樓給予其劇場許多名字。他有時說它是一個建構的精神或靈魂,有時說是有窗子的靈魂。他宣稱所有人類靈魂可以構思且無法以肉眼看見的,我們可以在專注的沉思之後,透過特定的物質符號表現出來。如此觀眾可以在一瞬間感知到深藏在人類靈魂之下的內容。而是因為這種物理性的視域他將其稱之為劇場。」(Daugeron, 2009:72)
記憶劇場的空間設計也令我們想到同樣自文藝復興時期起盛行於歐洲的解剖劇場(Anatomical Theatre /Operating Theatre)。解剖劇場是專為解剖教學而設計的特殊教室,通常有一高聳圓頂,室內呈劇場形式,舞臺在中央,周圍是環形的階梯座位,舞臺上安放著一張桌子,用於擺放被解剖的人或動物屍體,學生和觀察者都圍坐在階梯座位上,劇場周圍懸掛著人體和動物的骨架,以及解剖示意圖。在劇場中上課成為十六世紀歐洲解剖學教學的一種流行形式。到了十七世紀,解剖劇場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個焦點。在歐洲,早期大學附屬的解剖劇場由於公開解剖而逐漸成為旅遊景點。從荷蘭萊頓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倫敦,這些不同尋常的城市向熱情和感興趣的公眾敞開了大門。萊頓大學的解剖劇場初建於1596年前後,是最著名的一間。不僅有學生,也有非學生來參觀,入場並要收費。解剖劇場的風行一直到十九世紀才逐漸趨緩(Mandressi, 2019)。
目前文獻可考的十六至十七世紀著名的收藏多集中在義大利、法國與奧地利。有別於之前的收藏主以王宮貴族為多,此時期的收藏主多是學者。著名者如十六世紀Verone的Francesco Calceolari, Bologna的Ulisse Aldrovandi, Rome的Michele Mercati, 以及Naples的Ferrante Imperato 。十七世紀有Rome的 Kircher, Milan的Manfredo Settala, Verona的Lodovico Moscardo 以及Bologna的Ferdinando Cospi。在法國,著名的收藏有Bernard Palissy (1510-1590)以及Fabri de Peiresc (1580-1637)。Giuseppe Olmi以Calceolari的收藏說明奇收藏室的配置是功能性而非象徵性(Olmi, 1985:3)。這些收藏室與弗朗切斯科一世的收藏室不同之處在於,後者的收藏放在封閉的櫥櫃內,而這些學者的收藏多放在方便拿取的抽屜或層架之內,其無所保留全部展示的意圖非常明顯。
Laurencich-Minelli以十六世紀的學者Antonio Giganti為例,說明這位收藏家留下的檔案如何得以令後人重建其收藏的配置。Giganti的收藏是百科全書性質的,且包括以我們今天的學科分類會歸之於自然科學、人類學以及考古學的物件,其中包括許多來自中東以及美洲的收藏品。在配置方面,Giganti顯然希望填滿每一個空間,不區分自然物與人工物,且希望在陳列上達到對稱的效果(Laurencich-Minelli, 1985:22)。Laurencich-Minelli指出兩種對稱的法則:交替的小對稱(alternate microsymmetry)與重覆的大對稱(repeating macrosymmetry)。前者指的是同樣的物種或物件,不會並排,而是與另一種類似但不同的物種或物件交替陳列。如此可以在視覺上達到有變化不單調的效果;後者指的是依照主題,將其中的物種或物件陳列在同一區。透過這樣的陳列法則,將自然與人造的所有物件以容易觀看與拿取的方式配置在收藏室的每一角落,呈現理想中的「自然劇場」(theatrum naturalia)。隨著物件的堆積,次序與分類成為收藏家費心的焦點。
收藏的歷史與思想的歷史為一體兩面。十八世紀收藏從珍玩走向有方法論的次序。物件的系統與分類法的系統互為因果。系統分類的工作在林奈手中得到最高度的體現,其在植物學的方法也被動物學、乃至礦物學所採用,並因此影響到博物館與植物園的陳列規劃。在法國,保存到目前的三個自然史博物館收藏櫃見證了此時期的分類法原則:收藏在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中央圖書館的de Bonnier de la Mosson (1702-1744)、收藏在 la Rochelle博物館的de Clément Lafaille (1718-1782) 以及收藏在史特拉斯堡動物博物館的de Jean Hermann (1738-1800)(Van Praët, 1996)。
櫥櫃的發展應可說隨著主題性展示在十九世紀的出現而結束。後者導致展覽與收藏功能的區別,博物館不再將所有收藏的物件分類展出,而是挑選特定物件將其依照特定的論述陳列。最早期的主題展包括1880年代的Pitt Rivers Museum以及巴黎自然史博物館的比較解剖學與古生物學館。展覽不再是「物件的圖書館」而更成為一個與觀眾溝通的場域(Van Praët, 1996)。這樣的走向隨著透視模型(diorama)的出現更加顯著。製作一個透視模型時,並非是挑選收藏中的物件,而往往是為了展示製作展品,因而展品的教育性與戲劇張力便更為重要。
(二)型態:園林
園林在許多文明中都具有效法自然以及呈現理想自然的角色。除此之外,歐洲的園林尚具有陳列的功能,與室內的收藏室形成彼此互補,共構展示系統的關係。Hunt指出,十六世紀英文的cabinet也可以指「園林內的小屋或涼亭」(Hunt, 1985:267)而這種園林與居室的密切關係,最初可上溯至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如梅第奇宮殿便在園林陳列古代的雕像,而涼廊(loggia)、柱廊(portico)連結並銜接了室內與戶外。在Florence的Orti Oricellari園林,古代雕像與古典文學中提到的植物一起展示。同樣地,在Mantua的Isabella d’Est也在其宮殿中規劃一間同時用來展示收藏並研究教學雕塑、繪畫、珍貴石頭的studiolo以及園林。而十六世紀教宗的Villa Belvedere是各地爭相模仿的典範(Hunt, 1985:269)。
這些園林,有的布局相當簡單,有的則由專人設計的極為複雜。在萊頓,1599年設置的Ambulacrum同時包含一座植物園、一座自然史博物館、溫室(orangery)以及進行化學實驗的場所,其植物園的布局便呈現簡潔的幾何型。在園林中,種植著各種珍貴稀罕的植物與花卉,以盡可能體現自然的豐饒。有著模擬動物造型的石頭與人工的雕像配置在園林中,有如一座戶外博物館,呼應著文藝復興以來一個常見的主題:人與自然之間時為和諧、時為競爭的關係。十七世紀,園林藝術依舊是義大利引領風騷,有著精心設計的水利系統與石頭造景,亦即所謂的奇石(grotto)。Hunt指出園林整體構成一個古典的記憶劇場:其古代雕像緬懷著古代黃金時期,而自然史的陳列(包含植物與動物)是一個失落的伊甸園的記憶劇場(Hunt, 1985:272)。
十七世紀時植物的分類還不完整,類似條目的記述,尚缺乏系統性(Schnapper, 2012:83)。譬如植物學家與藥劑師Paul Contant (1562-1629)的分類為水果、木頭、樹皮、花、根、橡膠。在收集的植物內容方面,特別受到喜愛的是花卉如:水仙、康乃馨、秋牡丹以及最重要的鬱金香。另外柑橘、橘樹、檸檬樹等果樹也是收藏的重點。對於此時的植物學家而言,最感興趣的地方是異國的特色,並希望能將自己的花園建置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小宇宙。
在法國,法蘭西一世(François 1er)的楓丹白露宮(Fontainebleau)有一間皇家收藏室(Cabinet royal),但記載非常有限。Henri IV熱衷收集稀有物件,請Jean Mocquet (1575-1617)負責規劃一座珍玩室(cabinet de curiosités)。Henri IV也積極收集植物,委請Jean Robin (1550-1629)規劃,並於1593年在Montpellier設置法國最早的植物園。後者也負責規劃凱薩琳˙麥迪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的杜樂麗宮(Palais des Tuileries)的花園。另外,從文獻可知羅浮宮最晚在1603已經設置古代廳以陳列古代的雕像,其中有新購也有從法蘭西一世處移來的舊藏。
法國在路易十六之前最重要的收藏家為奧爾良公爵(Gaston Duke d’Orléans, 1608-1660), 其收藏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歷史方面的錢幣(médaille)和刻石(pierre gravée),二是自然史方面的植物(特別是花卉)以及動物的插畫。奧爾良公爵將其植物園交由Robert Morison (1620-1683)管理。其自然史收藏部分由大臣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收購,發展成為一間專門的珍玩室(Cabinet d’histoire naturelle),後者經過不斷拓展,成為日後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本文拉雜記述歐洲自文藝復興到十七世紀時期的自然史收藏發展,其中可見珍玩室的櫥櫃與園林做為日後博物館室內室外展示的早期型態,甚至直接演變為自然史博物館,其中的收藏內容、配置方式、象徵意涵,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The Sculpture Garden of Cardinal Ceci, by Hendrick van Cleef III. National Gallery, Prague. (引自Impey, O. & MacGregor, A., 1985:270)
參考書目
- Alsop, J. (1982). The Rare Art Traditions: The History of Art Collecting and Its Linked Phenomena Wherever These Have Appea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Daugeron, B. (2009). Collections naturalists entre science et empires (1763-1804). Paris: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 Hooper-Greenhill, E. (1992).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Hunt, J. D. (1985). ‘Curiosities to adorn cabinets and gardens’, in: O. Impey & A.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House of Stratus, pp. 267-279.
- Impey, O. & MacGregor, A. (1985).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House of Stratus.
- Laurencich-Minelli, L. (1985). “Museography and Ethnographical Collections in Bologna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O. Impey & A.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House of Stratus, pp. 19-27.
- Lach, D. F. (1970).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One: The visual Ar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ndressi, R. (2019). “Anatomy Theater: The Order of Curiosity”, in: T. Garcia & V. Normand (eds.), Theater, Garden, Bestiary. A Materialist History of Exhibitions. Sternberg Press, pp. 67-74.
- Olmi, G. (1985). “Science-Honour-Metaphor: Italian Cabinet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O. Impey & A.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House of Stratus, pp. 1-17.
- Pline l’Ancien, (1999). Histoire naturelle. Les Belles Lettres.
- Schapper, A. (2012). Le géant, la licorne et la tulipe : Les cabinet de curiosité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 Flammarion.
- Van Praët, M. (1996). “Cultures scientifiques et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en France. Hermès la Revue, 20 : 143-149.
- Yates, F. A. (1966). The Art of Mem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